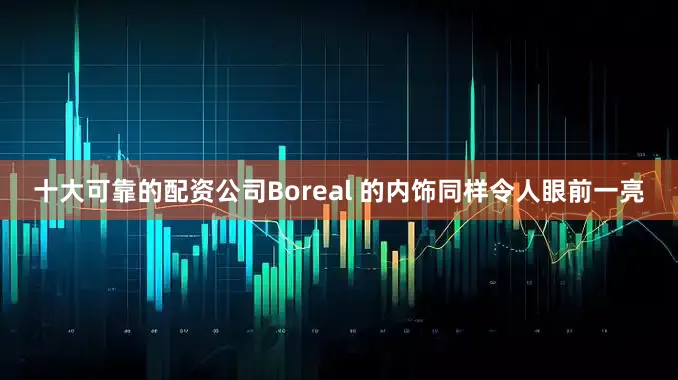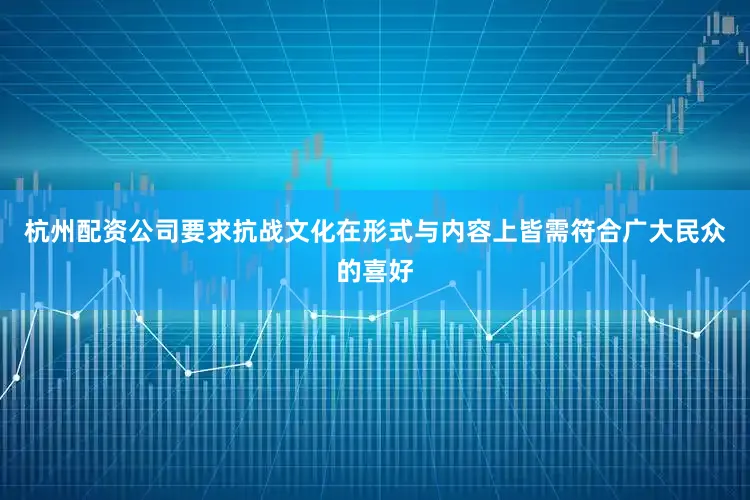

抗日战争,一场中日两国在力量对比悬殊下的民族冲突,日本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中国则凭借着道义和政治上的优势。毛泽东曾深刻指出:“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交织融合的复杂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4页)“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首先要依靠武装起来的军队。然而,仅有武装军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拥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内部、战胜敌人不可或缺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页)鉴于此,建立我们文化战线的队伍,广泛开展各类文化抗战活动,便成为了赢得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
文化抗战,作为我国文化界爱国志士运用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电影、报刊、电台等多元文化载体,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抗争,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线的抗战并肩,同属伟大抗日战争的不可分割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凝聚民族精神、振奋抗战斗志、激发民众士气的强大武器,更催生了诸如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文学、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丰富的文化形态与现象,共同构筑了抗战文化的壮阔画卷。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基于全面抗战的指导思想,明确了自身的文化抗战理念,引领并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抗战运动之中。
“文化、军事与政治三者相融,方能成就革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文化与军事、政治相结合,才能构成革命军队的战斗力。”(详见《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

毛泽东挥毫题写的“繁荣抗战文艺,鼓舞军民士气,共争最终胜利”。
如何构建文化抗战的框架?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应“构筑文化运动中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目标一致,即抵御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民族投降主义,以及反对复古主义。这一观点源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的第135页。毛泽东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首先与党外的所有文学家艺术家联合,无论是党的支持者、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创作者,还是所有支持抗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文艺创作者。”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第867页。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其中专门论述了建立抗日文化队伍的重要性。概括而言,即联合所有愿意参与抗日的文化人士、团体和流派,形成一个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朱德进一步阐释道:“掌握艺术技能,以文字、歌曲、绘画、音乐、戏剧等作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战争。”(出自孙国林《朱德与抗战文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瓦窑堡会议旧址。
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其中明确阐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运动的四大主要任务。该文件特别强调,在革命根据地内,应广泛吸纳知识分子以及各类专家学者,让他们参与到抗战的各项工作之中。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针对部队文艺工作制定了专项政策。同年1月,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指出:“部队文艺工作的核心方针,是首先团结并培育那些具备战斗生活经历的文艺专业人士,使他们能够通过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多种艺术形式,将民族战争中的各类现实生活(包括民众和将士的英勇抗争,以及日寇、汉奸、投降派和顽固派等各方的阴谋与诡计)生动地展现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第20页)这一方针对于强化军队文化工作,提升军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团结人民、启迪人民、对抗敌人、击溃敌人的坚强武器,协助人民齐心协力与敌人抗争。”

延安 鲁艺。
彼时,我国抗战文化流派纷呈,而真正引领潮流的,乃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其具备三大鲜明特色:首先,民族性突出,旨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其次,战斗性鲜明,抗日战争不仅是关乎国家命运的民族战争,亦是关乎中华文化命运的文艺之战;再者,大众性显著,要求抗战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皆需符合广大民众的喜好,贴近民众的情感。其杰出代表为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原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该篇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应构建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的精辟总结,也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先进文化思想。
音乐:“众志成城唱响”
梁启超曾精辟指出:“若欲重塑国民之品格,诗歌与音乐便是精神教育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战音乐应运而生,肩负起拯救民族、恢复国家的大任,成为贯穿抗战岁月的一道璀璨风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
在东北沦陷之际,由地下党组织引导的左翼文艺团体及进步文艺人士,掀开了抗战歌曲创作的热潮。韦翰章、陈洪、适群、黄自等先锋人物,自1932年起陆续推出了《红旗飘飘》、《热血歌》、《驱逐敌寇出国土》、《战歌》、《冲锋号》、《上前线》等作品,激昂地呼唤“旗帜飘扬,马蹄声急,肩扛枪械,腰别刀剑,热血如潮,英勇男儿报国在今朝”,引领民众觉醒,明确“锦绣河山,谁为主人?我们四亿同胞,一致抗战,报仇雪恨。家可毁,国必保”。此后,聂耳、冼星海、吕骥、张曙、孙慎、周巍峙、贺绿汀、麦新、张寒晖等众多革命音乐家涌现,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和爱国情怀。如《松花江上》抒发了东北人民家破国亡的悲愤,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义勇军进行曲》、《华北抗战歌》以激昂的旋律传递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与民族抵御外侮的决心;《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有力地反驳了蒋介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的言论,激发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决心;《大刀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士兵们抗战的斗志。特别是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其坚定的节奏和欢快的旋律,彰显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的坚强意志。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被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全民族抗战的硝烟弥漫之际,宣传、动员与组织民众投身战场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歌曲的创作热潮。在陕甘宁边区以及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创作演唱队伍迅速崛起,主要由专业音乐家牵头,辅以业余音乐创作者和民间歌曲爱好者。他们作词、谱曲、创作、教授与演唱,形成了一种无缝衔接的工作模式。从军营到民间,从烽火连天的战场到紧张繁忙的敌后生活,处处都有音乐工作者忙碌的身影。冼星海曾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应当将救亡音乐作为武器,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他们亲身体验、耳闻目睹战争的残酷与时代的精神,将之转化为强烈的抗战情感。无论抗战的任务是什么,相应的歌曲便应运而生,既有揭露与控诉,也有歌颂与讽刺,既有悲壮的旋律,也有欢快的歌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些歌曲不仅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激励了前线将士英勇杀敌,也为民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
在抗战的中段,国民党内的一股顽固势力消极抵抗日军侵略,却积极反共,接连掀起了三次反共的高潮,对解放区实施包围和封锁。面对此情此景,中国共产党展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这一时期涌现的《起来反内战》、《打击顽固分子》、《茂林惨案》、《骂何应钦》等歌曲,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冲突、残害抗日同胞的恶劣行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经典选曲《游击队歌》的精彩剧照。
在这个时期,众多抗战名曲如《游击队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团结就是力量》、《长城谣》、《到敌人后方去》、《毕业歌》、《新编九一八小调》、《胜利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同时,还有《延安颂》、《南泥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民主之花》、《减租会》等歌曲,它们赞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辉煌成就。
随着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根据地涌现出一批鼓舞人心的反攻歌曲,诸如《前进!解放区的军民》、《反攻进行曲》、《我们是反攻的主力》等。进入反攻阶段,抗日军民士气振奋,捷报频传,歌曲《我们的旗帜到处飘》、《抗日战争大胜利》等四处传唱,洋溢着抗日军民的欢愉与激动。
“抗战胜利后,曾有日本人在台北阳明山宣称,中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日本,并非仅仅是凭借军事战略和战术,而是倚赖抗战歌曲所激发的强大心灵力量。”

冼星海在延安执导《黄河大合唱》排练。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其气魄雄浑、情感深沉,堪称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其影响力历久弥深。此曲以黄河为象征,赞颂了民族抗争的英勇事迹与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将民族危亡的痛楚化作中华儿女的怒吼之声,激励着无数抗日战士与爱国青年,他们高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怒号”,勇赴抗战的沙场。
《黄河大合唱》是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亦即民族象征的深情赞颂。这部作品诞生于我国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深刻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集体精神需求。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抗战岁月中最激昂的旋律。毛泽东听后连声赞叹:“好!好!好!”周恩来则亲笔题词:“怒吼抗战,谱写民声!”
戏剧表演中,舞台上呈现着激昂的抗日戏曲,而观众席上则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抗日口号声。
“开一个两小时会议的成效,不如上演一部好剧;上一堂课的效果,不如举办一场晚会。”中国共产党通过引导和影响各种文艺团体以及抗日剧社,有效地推进了动员、宣传和统战等工作。正如朱德在晋东南各剧团代表座谈会上所强调:“戏剧是宣传群众的有力工具,每一位戏剧工作者都应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启迪和教育他们,激发他们投身抗战;戏剧应当更多地展现抗战期间各地英勇斗争的悲壮事迹。”(详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52页。)
自1937年起,延安便设立了人民抗日剧社总社,下辖中央剧团、平凡剧团、战号剧团、青年剧团等多个团体。他们上演的剧目,诸如《亡国恨》、《察东之夜》、《李七嫂》、《矿工》等,皆洋溢着浓厚的抗日气息,彰显了人民的团结与力量。这些作品风格贴近群众,台词通俗易懂,每一部戏都能深入人心,深受群众喜爱。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将抗战戏剧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戏剧工作者们积极组织抗日戏剧公演,有效地鼓舞和启迪了广大民众。
“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红军战士与苏区民众趁势响应,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欢迎友军,共同抗日!”一时间,演出现场呈现出“台上演抗日戏,台下呼抗日口号”的感人场景,有力地促进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人心,对于促使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战斗剧社于晋绥地区倾情呈现六幕话剧《把敌人挤出去》。
在众多抗日敌后根据地里,剧团如星河遍布。成立于1937年的抗敌剧社,实则是对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的雅称。在该剧社举办的300场纪念活动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鲜明地阐述了剧社的定位与使命:“剧社必须坚守党性、阶级性、军事性和战斗性的原则。每位社员都需致力于党的宣传、抗战的宣传,激发军民的战斗意志,积极参与部队与群众工作。”(刘佳、胡可等:《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页)从1939年至1942年,抗敌剧社创作并演出了众多活报剧。1939年,他们推出了《青年进行曲》、《国际风云》及《迎接相持阶段到来》。在同年反“扫荡”胜利后,他们又编排了揭露敌人罪行的歌活报《在这块土地上》、舞活报《过难关》以及反映空舍清野斗争的舞活报《空城计》。1940年初,为号召民众投身春耕生产,剧社首先演出了小型歌活报《春之歌》,随后又创作了以大水灾后自救为主题的大型活报剧《生产大活报》。为了推广边区政府的二十条施政纲领,他们还创作了深受群众喜爱的《王老五逛庙会》。为纪念1941年的“三八妇女节”,剧社编排了大型活报剧《哭与笑》,生动展现了新旧社会妇女命运的反差。当年秋季反“扫荡”之后,剧社又创作了以童话为形式的歌舞活报剧《乐园的故事》,通过这种形式反映了反“扫荡”的斗争历程。
抗敌剧社作为晋察冀边区抗战戏剧的中坚力量,固然举足轻重,然而并非独此一家。边区各分区亦纷纷设立剧社,诸如第一军分区的战线剧社(下设三支分队)、第二军分区的七月剧社(又名奋斗剧社)、冀中军区的火线剧社、第六军分区的前锋剧社、第八军分区的前卫剧社、第九军分区的前哨剧社,以及回民支队的抗敌剧社等。即便尚未建立剧社的军分区,也均设有宣传队。此外,民间团体剧社与乡村剧社亦为数众多。在部队及地方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引领下,自1943年起,晋察冀的北岳区和冀中区便涌现出3000多个活跃的村剧社。仅太行区的15个县便拥有农村剧团600余个;晋东南区的农村剧团亦达170多个,创作剧本近千种。(摘自《文化与抗战》,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18页)乡村剧社的表演形式以秧歌剧为主,亦不乏传统戏剧。其内容涵盖广泛,既有英雄事迹,也有敌人残暴行径和敌占区人民的苦难,还包括反特务、锄奸、争取伪军等多个方面。

◆抗敌剧社儿童剧队合影。
在众多抗日根据地,各式规模的抗敌戏剧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晋冀鲁豫地区,太行山剧团、火星剧团、大众剧团等纷纷成立;晋绥地区则出现了战火剧社、战力剧社等团体。1940年10月,费北文化工作座谈会之后,山东地区的各剧团纷纷进入剧本创作的高潮,这一热潮持续至1942年5月,最终在联合大公演中达到高潮。而在华中地区,仅1937、1938两年间,部队剧团的演出就达到了七八百场,创作的剧本总数更是超过了200部。
彼时,我方与敌方在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交锋频仍,如同遭遇战般。1942年春季,晋察冀边区抗敌剧社挺进敌占区深处的定襄、忻县、崞县等地,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攻势。恰逢日伪军携带旧剧班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日伪军在白家庄上演戏剧,而抗敌剧社则于南庄举行演出,双方的警戒哨彼此可见。日伪军邀请山西的二三流戏班表演《春秋配》、《玉虎坠》、《哭灵堂》等封建题材的戏剧,以及日本人的训话、新民会的演讲,以及话剧讲习所毕业生的文明戏等。而抗敌剧社则献上了《人间地狱》、《弃暗投明》等反映抗战的戏剧作品,以及歌曲、相声等节目,并举办了美术和照片展览。敌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总计耗费白洋3020元,由白家庄等四村分摊。相较之下,抗敌剧社仅用“煤油8斤、洋蜡1包、火柴1包”,总计洋边币42元整。如此对比之下,抗敌剧社不仅在宣传内容上占据道德高地,而且在经济上也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美术:用画笔守护祖国风光
自抗战爆发之际,美术界同仁在共产党引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炽热爱国之情,纷纷投身于充满热情的群众组织,奔向炮火连天的战场,亦踏入偏远的城市和古老的乡村。他们运用多样的材料、媒介、形式和创作手法,以保卫祖国壮丽河山为己任,传递出团结一心、斗志昂扬的坚定信念,激励着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发向前。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我国文盲率较高,民众整体文化素养相对较低。在这样的国情背景下,美术以其直观、通俗的特性,在众多艺术门类中展现出独特的传播优势。其中,木刻版画因其就地取材、制作成本低的特性,以及便于大量印刷,成为了普及宣传的重要工具;年画作为传统艺术形式,为民众所熟知,将其与抗日主题相结合,易于民众接受;而漫画与宣传画则以直观形象、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深入人心。此外,美术的表现场地非常灵活,既可在纸张、布料、墙面、树木、石头上创作,又便于张贴与悬挂,甚至有些作品还可移动。
在全面抗战的初期阶段,国共两党摒弃旧怨,携手共抗外敌。我国美术界亦遵循国共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投身创作,传播团结抗战的理念,抵制分裂与投降的倾向。以延安鲁艺教授蔡若虹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为例,其创作的招贴画中心描绘了一位扭曲面容的日本军官在汹涌的海面上漂浮,上方则是一位力大无穷的人物,正拉着与粗壮铁锚相连的铁链。这幅画以象征手法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坚定意志,以及日本侵略者将被淹没于人民战争的无尽洪流之中。鲁艺的套色木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亦颇具代表性,画面中,众多军民在国共两党的旗帜下庄重地屹立,仿佛在庄严宣誓捍卫国共团结,作品深刻揭示了国共合作顺应民心、深得人民拥护的真理。
受限于文化素养,广大民众的艺术鉴赏与美术家的艺术追求之间往往存在显著分歧。鉴于此,美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迅速确立了以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为导向的新写实主义美术理念。他们坚守写实主义,抵制模糊抽象,运用具有较强叙事性、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艺术形式,内容主要聚焦于战争、军民协作以及百姓日常生活等方面。这一艺术观念与表现手法赢得了领导和民众的普遍认可。

彦涵基于其亲身经历的“扫荡”行动,创作了木刻画《当敌人搜山之际》,完成于1943年。
木刻画凭借其大众化、宣传性强、教育性突出等优势,在抗战时期的美术作品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创作形式便捷易行,可大规模印刷,便于携带,是成本低廉且传播迅速的战斗利器,完美适应了物资紧张的战时环境。木刻画以其直观的图像、鲜明的叙事特点,通过黑白对比与简洁的线条来强化主题,即使无需文字,也能有效传递信息。以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彦涵创作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为例,画面中,八路军战士在民众的扶持下从战壕中升起,手持轻机枪与敌人展开激烈对抗。画面中紧张的人物动态和场景描绘,生动地展现了敌我双方在“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中的激战情形。
木刻画在创新中融入了民间传统,例如借鉴了年画的形式,如门神画,将抗战内容与之结合,既保留了传统审美的精髓,又赋予了作品新的内涵。彦涵的《保卫家乡》(由《八路军和民兵》与《妇救会员和儿童团员》两幅画作构成),胡一川的《军民合作》、《开荒》、《破路》,以及杨筠的《织布》、《纺线》等年画,因其新颖且价格低廉,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被赶集的民众一抢而空。这一消息传开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下令将他们的作品寄往重庆,以便在大后方传播。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在观看作品后,称赞它们是美术服务于抗战、服务于群众的典范,并亲自给木刻团写信以示鼓励。彦涵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1940年创作的《保卫家乡》年画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艺术表现力,于1944年创作了《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年画。他借鉴了中国传统门神的创作手法,以战士形象取代了门神。民主人士李公朴在考察晋察冀后记录道:“在每一个村庄,你都能看到家家门上贴的门神不再是秦叔宝、尉迟恭,而是写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闪亮大刀的自卫队队员英姿。过去由天津运来的《麒麟送子》、《老鼠娶妻》等年画,已被《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抬伤员,送茶饭》、《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等抗日年画所取代。”(见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6页。)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有组织地涌现了一批抗日连环画的创作与改编。何云所编绘的《狼心喋血记》与《百劫英雄》两部作品,以其鲜明的反日反侵略主题,在广场上向民众展示,产生了显著的政治效应。劫夫的木刻连环画《如此扫荡》刊登于《晋察冀画报》,生动描绘了日军气焰嚣张地进入抗日边区“扫荡”,却在遭遇八路军伏击后落荒而逃的狼狈情形。整套画作层次分明,情节跌宕起伏,将幽默融入图文之中,展现了敌后根据地军民坚定的斗争意志、无私的牺牲精神以及灵活的战术策略。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胡一川、罗工柳、雏雅、刘韵波等人创作的《抗战十大任务》木刻连环画,广泛传播了八路军抗战的核心任务。木刻团团长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则普及了游击战术和英勇事迹。李少言的《日军守备队的生活》、《八路军一二〇师在华北》,王朝闻的《姆妈》,古元的《走向自由》、《新旧光景》等木刻连环画,同样赢得了民众的喜爱。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木刻连环画,生动再现了五位英雄誓死抵抗、宁折不弯的壮烈事迹和光辉形象。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等美术工作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踏入烽火连天的战场,深入饱受苦难的民众生活,用画笔和刻刀描绘战争的残酷,赞颂英勇无畏的中华儿女。他们以亲身经历的战斗岁月和满腔热血,创作出了众多感人至深、质朴无华的美术作品,为新四军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力量。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每师均设立了服务团,下设绘画小组,成员人数各异。部分师部与地方抗日根据地政府携手共建艺术学院,从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绘画人才。

刘建庵所著的《我们的武器——笔杆》一文,发表于1938年9月1日的《解放日报》。
《漫话漫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新四军的美术创作形式丰富多样,涵盖了宣传单、连环画、年画、书籍装帧以及货币图案等。在美术用品极度匮乏、印刷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美术工作者们凭借智慧和创造力,克服重重困难,发明了墙画、布画、传单画、油印画等多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其中,墙画创作起步较早,数量亦颇为可观。每当新四军行动,绘画组总是率先出发,边行军边创作。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能够利用的墙面,都会绘上墙画,用简洁明了的绘画形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建国十大纲领。布画亦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绘画组创作了众多巨幅布画,如《屠场》、《夺取敌人武装武装自己》、《打鬼子保家乡》、《军民合作打日本》等,这些作品激发了无数群众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坚定决心。
文学:笔刀文弹
在抗战烽火中,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并组织了众多文学工作者,他们手持笔杆,英勇投身于抗击侵略者的斗争。臧克家以诗句抒发了众人的心声,在《我们要抗战》一诗中,他呼唤道:“诗人啊,请敞开你的嗓音,让喇叭的声音响彻云霄,唯有高歌战歌,你们的诗句才会显得寂寥无声。”
在抗战文学的创作领域,饱受沦陷之苦的东北作家群体勇立潮头,他们的笔下流淌着对故土的深切怀念与流离失所的哀歌,深刻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位于晋、陕、豫三省交汇处的潼关,面对黄河彼岸的风陵渡,萧红、端木蕻良等作家挥毫泼墨,创作了《黄河》、《风陵渡》等作品,塑造了极具艺术感染力的黄河形象,展现了全民共赴国难的抗战意志。作品中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恰似黄河波涛拍击岸边的壮阔景象。

1942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与在场文艺工作者共同留下了珍贵合影。
自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来,文艺界同仁们踊跃投身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充满战斗力和感染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对广大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真实记录,也有对人民战士英勇无畏和无限忠诚的生动描绘,更有对根据地崭新生活和斗争的深刻反映。巍峨的太行山,作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和坚实后盾,汇聚了众多杰出的文艺人才。李公朴、卞之琳、丁玲、周立波、何其芳、沙汀、周而复、杨朔、刘白羽、吴伯箫、陈荒煤等纷纷前往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创作了如卞之琳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晋东南麦色青青》、丁玲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何其芳的《星火集》、《星火集续编》、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南下记》、周而复的《晋察冀行进》、《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等众多珍贵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太行山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画卷。1937年,桂涛声在山西陵川县创作的《在太行山上》,后由冼星海在武汉谱曲,成为传唱大后方的抗战名曲。这首由诗作衍生的抗战名曲迅速传遍各抗日根据地,激励着无数民众投身抗日战场。
根据地小说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马烽与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刘白羽的《五台山下》、孔厥与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无不生动展现了抗战斗争的艰辛与英勇,以及军民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壮烈情怀。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描绘了抗日时期农民与地主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小二黑结婚》则记录了根据地青年男女反抗封建束缚、追求美好生活的斗争历程,赞颂了民主政权的伟大力量,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活跃于冀中白洋淀水域的英勇水上游击部队——雁翎队。
文学界同仁亦不遗余力地推广我抗日英雄的崇高形象。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源自沈重所著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该作品一经《晋察冀日报》刊登,便使得五壮士的英勇故事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雁翎队》则是作家穆青于1943年创作的一部作品,该作以白洋淀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为核心,生动描绘了一群冀中水上勇士的英勇形象,展现了白洋淀人民深厚的乡土情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诗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反抗奴役的坚强意志,摒弃了冗长的叙述和迁回的表达,将事实与推断直接呈现,虽然诗句简短,却极具震撼力,其力量远胜于冗长的政治鼓动词。

1938年8月7日,柯仲平、田间、林山等人士,代表边区文协战歌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共同发起了一场名为延安街头诗的运动。此次运动中,《新中华报》特别转载了《街头诗运动宣言》。
在散文领域,茅盾的《白杨礼赞》与《风景谈》尤为广为人知。《白杨礼赞》以白杨树为象征,赞颂了北方抗日军民的英勇;而《风景谈》则满怀激情地描绘了延安军民的炽热战斗生活。何其芳的《星火集》、巴金的《无题》、李广田的《圈外》、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以及夏衍的《此时此地集》等散文集,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抗战时期,报告文学创作亦十分活跃,涌现出诸多佳作,如丘东平的《叶挺印象记》与《王凌冈的小战斗》、碧野的《太行山边》、萧乾的《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以及刘白羽的《游击中间》。
结语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它增强了民众对共产党和根据地的认同,为日后国共两党对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心理基础。
文化繁荣,国家方能昌盛;文化强大,民族才能自强。在现今推崇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时代潮流中,文艺工作者们亦应致力于创作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精品。他们在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应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底蕴,从而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积极作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风采,为民族复兴贡献独特的文化力量。
广源优配-配资门户资讯-配资论坛-配资炒股平台首选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网站平台推动建立公平有序行业秩序
- 下一篇:没有了